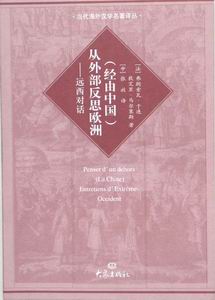 近来集中探研德国古典时代前后的“世界命题”,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无法孤立地在德国文化语境中思考问题。有几个大的维度必须关注,一是当时的“东方镜像”,即包括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思想资源在
近来集中探研德国古典时代前后的“世界命题”,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无法孤立地在德国文化语境中思考问题。有几个大的维度必须关注,一是当时的“东方镜像”,即包括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思想资源在
虽然,十七世纪以来的世界秩序是由英国的不断崛起和渐趋衰落而形成主线的,但在欧洲大陆,情况并非如此。德法之间的消长,始终贯穿着欧洲历史发展的主脉。可以说,德法两国的碰撞基本上构成了推进十八~二十世纪欧洲历史的主要动力。这一判断不仅建立在军事―政治层面,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十八世纪被称为“光明世纪”,即是以法国思想文化的灿烂绚丽为中心的。近代法国思想之源,应追溯到笛卡儿,其鼎盛时期的巨匠有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而同时,德国则孕育着一个行将崛起的思想高峰――古典时代(古典哲学与古典文学双峰并峙)。更有趣的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中后期)法国思想如日中天,不仅有福柯、布迪厄、德里达这样的大师在前,而且又出现了于连;而稍前,德国则展示了现代思想史上波澜壮阔的景象,即以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等为代表的德国现代哲学。在我看来,于连不仅是这一传统中的异类,更可能是一种“范式转换”的代表和前驱者。因为,法、德(或者说“整体西方”)的大思想家,在此之前,少有对“异质文明”的深入研究者,尤其是像东方学家这样的人物。这虽然并不妨碍法、德思想的“璀璨夺目”,但也难避免“一叶障目”“自我中心”的问题。
于连(Francois Jullien)的学术背景使此种危险降到最低。他先于巴黎高师学古希腊哲学,后转向汉学。他清晰地表达了其学术研究背后的文化情怀:“哲学是扎根于问题之中的。为了能够在哲学中找到一个缺口(边缘),或者说为了整理创造性理论,我选择了不是西方国家中的中国,也就是相异于西方希腊思想传统的中国。我的选择出于这样的考虑:离开我的希腊哲学家园,去接近遥远的中国。通过中国――这是一种策略上的迂回,目的是发现我们西方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打开思想的可能性。”(杜小真:《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关于法国哲学家于连的研究》,第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段话作为学人的“夫子自道”兼及关怀与策略,值得细加剖析。首先看于连的关怀,其目的在于“打开思想的可能性”,而什么才是当代的思想可能性呢?就是以未能向西人呈现的视角来发现“新意”。进一步说,于连在学术上有宏大的抱负,即建构出“创造性理论”。应该说,从“思想”到“理论”,于连的思路是清晰的。大的目标方向确定之后,接着就是具体的策略问题。时代发展到今天,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已汗牛充栋,进入程式化的“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状态容易,但想取得思想上些微的实质性进步谈何容易?更何况是具有宏大抱负的“创造性理论”的发明。于连在其深厚的西学传统(主要以希腊哲学为根基)烛照下,选择了“取异”的策略,即越是独立、越是异质性明显的文明,越符合他的入手标准。这充分表明了于连作为一个思想者兼学人的可贵品质,既不乏思想家洞烛机先的敏锐,又具备学问家脚踏实地的实证意识。
经过这番比较选择,于连选择了“中国”。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再仅是一个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概念对象。于连的思路相当明确:“从严格意义上讲,惟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中国的意义,就是其巨大的“异质性”。
这个判断大致不错,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便如于连所言,“直到十六世纪,中西尚没有真正的交流”(于连《答张隆溪》,载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第13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我们仍不能忽略这样一个现象,作为“印欧语系”的重要国家,“印度、阿拉伯及犹太文化均同欧洲历史有联系”(同上第132页)。而印度作为重要的中间区域,它与欧洲和中国之间,都有相对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而“中印文化互动”问题,我们研究得太少,但实际上它非常重要(可参见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尤其是佛教东来之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的“质性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样的文化流播轨迹史,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很难说纯正的国族文明是什么,它真就不掺任何外来文化?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毕竟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更何况,再进一步追问,中西之间的交流岂能仅从十六世纪算起,景教东传即使影响不那么显著,但早已将中西交流的历史推向一个相当靠前的起点。不过,对于这些细节问题,暂时不做追究。
此处值得注意的乃是汉学家角色的呈现。实际上,综观历史,真正的大思想家,不可能将视阈局限于狭窄的文明一隅,而总是力图有宏观的天下气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都是如此。但由于不通语言,他们对中国的描述即便不乏洞见,也终究难称扎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Penser d'un dehors?la Chine?-Entretiens d'Extrême-Occident)的思想史意义就显出来了。汉学专业的身份使于连的中国认知更具学术基础,而哲人的角色又使他能纵横驰骋,不为考据之学所累。
其实,这种路径并非于连独创,只能算是在其手中发扬光大而已。艾田蒲(René Etiemble,中译名又作安田朴(1909~2002)已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他是法国少有的同时涉猎中学和西学的“东方学家”,其立足点已在创发法国之思想。对这位前辈,于连说客气话“承认他作为同中国做比较研究的头号人物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所起的作用”,可话锋一转,基本是批评的立场,认为其从两方面“求同”的思路不可取。(第112~113页)出于学术立场的根本歧异,于连这样论述前辈并非“不可理解”。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对艾田蒲的学术思路多一点“理解之同情”,他曾明确表示:“我只想使已缩进法国中心论,或最多也是欧洲中心论之中的法国比较学研究,产生一种新动力和一个新的方向。”(〔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L'Europe Chinoise),第19页)而且他也足够客观,即便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重视,仍不忘强调:“但学者们也不应认为我把中国对欧洲的影响(这至少已有2000年的历史了)视为欧洲在历史发展中所受到的唯一影响。”(《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页)于连虽与艾田蒲学术立场迥异,但就学术策略而言,他是承继了艾田蒲的路径的。
尽管于连一再强调其西方代表的身份,但我仍要将其看作法国思想的代表。此书是以对话体出现的,大体说来,十章内容可归纳为三篇,“历程”:于连在中(包括香港)、日居留学习时代的中国认知与精神历险;“论哲学的迂回:中国工具”:通过回顾汉学学科史(尤其是法国汉学的演变与发展史)来追溯中、欧思想碰撞的源起与发展;“从东-西两端阅读”则尝试利用“中国工具”来反思欧洲,希望达致“创新思想”之未来前景。再外加“代序”和“尾声”。
对我来说,饶有兴味之处在于于连借助代序一篇文字进入“福柯的反应”,恰恰是对福柯的挑战,展示了于连的思想史宏愿。他勾勒出的法国思想家与东方交流的轨迹是从“巴特中国之旅”(1974)到“福柯日本之行”(1978);或许还有潜意识未加注的是,“福柯的日本对话”和“于连的留华时代”(1974~1978)。这才是更具有划时代思想史意义的事件。事实上,于连也通过其留华时代的描述,给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进程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尤其是在与世界相关的宏大维度上。
于连提到了钱锺书,在他看来,钱氏的研究是典型的“中国式”做法,“旨在满足于从文本到文本,声称省去了重新分类的工作”。于连一方面肯定钱氏的学养与其作为学者、小说家的成就,另一方面则对其研究策略提出根本上的质疑:“他的批评天才却只限于在一种没有结果的研究活动,至少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研究中‘串联’文本,因为他的研究是实验性的,严格地横向比较:中文的某一段使他想到了狄德罗(Diderot)的某一段,又使他想到了格拉西安(Gracian)或谢林(Schelling)的某一段,等等。因此,这仍是一种比较研究的形式”,接着他指出这种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毫无建构”。具体言之:“人们停留在一种‘自由衔接’的形式(正如常说的‘联想’),这种形式是不可靠的,甚至当人们想依此进行研究时,便自身解体了。”(第135页)
这段批评基本上是客观的,但最后一句不尽然。虽然强调从“中国入手”,于连还是难以避免地带着法国学者的特征,难以对钱氏的“中国心态”有“理解之同情”。钱锺书自己有过明确的理论思考,他说:“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如此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断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两者同样都是零碎的。”(《拉奥孔》,载钱锺书:《七缀集》,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版)钱氏的著作行文方式,明显受到诗话与笔记体影响。这其中一个暗含的理论判断就是系统不足取。不过,在我看来,因为大楼终有一天会坍塌就选择不做设计师只愿意做泥瓦匠,并非一个学人该做出的选择。于连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对于钱氏诗学的价值,于连却并未能充分认知。钱锺书的著作,貌似“自由衔接”,但其所蕴深意则远过于此,其撰《谈艺录》称:“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虽然是在“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聚蚁”的状态中所作,但决非仅是“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既是“销愁舒愤,述往思来”之作,同时更强调“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基本学术理念(《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序”,第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于连只看到了钱著表现出的外在一面,如旁征博引、学养深厚、诗话的表达方式等,故判其为“某种寻同的比较主义(comparatisme de la ressemblance)”,说他是“有一种使各种思想相碰撞的兴趣”(于连《答张隆溪》,载《中西文化研究十论》,第135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隆溪质问他“是否真把钱锺书的著作看过一遍,或者说看懂了几分”(《中西文化研究十论》,第122页),虽然过于苛厉了些,但确实也道出了西方汉学家的瓶颈问题――对高明异质著作的“疏离感”。其实,这也不仅是汉学家的问题,任何一个研治非母语、本族文化者,都极可能遭遇这样的困境。
不过,在我看来,这并非致命问题。因为,若论对民族风俗、习惯与文化的了解熟悉程度,当然还属“身在此山中”的本土人;可要论识判“庐山真面目”,却必须借助于外来者的“特殊思想资源”。作为“法国知识界精英”,于连的长处仍在于法国文化传统的自身资源。如何以法国的学术/思想传统(背后可扩展为欧洲、西方的大背景)来识判中国文化,并进而由此返观法国――西方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在那部著名的《圣人无意》,(Un sage est sans idée - ou l'autre de la philosophie)中,于连提出了“圣人无意”概念,具体解释为:“圣人不持有任何观念,不为任何观念所局囿。”他也在不自觉中将这种“中国概念”与西方传统进行比较:“圣人的头脑中不会先有一个观念(‘意’),作为原则,作为基础,后者简单说就是作为开始,然后再由此而演绎,或至少是展开他的思想。”(《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第7页,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他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表述此著的“言外之意”:“作者是在批判种种逃避和补偿,是在驳斥威胁着我们的未来的如潮般涌来的非理性主义。”(《圣人无意》,第4页)于连将中西文化关系简化为“圣人”与“哲人”的关系,即“智慧”与“哲学”的关系。这种“寻异”应该说是有创见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于连是针对法国与欧洲语境发言的,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于连的一系列解说,将它作为一种思路原封不动地引入到中国语境内来,就不免“南橘北枳”了。所以我认为,将张隆溪与于连争论的一个问题凸显为“中西文化”对立与否不是很有必要。作为重要的文化体系,无论中西,都有其可以独立延绵发展的性格与特征,也都有其沟通对话、互为依存的共同性基础。关键在学者如何调试自家的眼光与建构自己的论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于连借助中国重新进入欧洲的问题思考域,或反思西方,都是一种理性的学术/思想策略。必然会因语境差异而有所取舍,对此似不必苛求。
“求同存异”之说,听来很有道理。实际上,“思想建构”的核心仍在于“互为主体”“良性互动”。每个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其实都很难避免生存语境的实质影响(或直接或间接,甚至潜移默化),而这样一种学术/思想资源,又深深制约着他“面对世界”乃至“学术思考”的目光。哪怕再强调“世界眼光”和“普遍主义”的学者都是如此。实际上,于连主要凭借的,正是法国本身的学术/思想资源。譬如他批评钱锺书的标准,就基本上采用法国哲学的标准。哲学主要是讲求体系建构的,没有体系,只能算是零星的思想火花。但钱锺书归根结底也只是个文学批评家,他不是史家,更非哲人。而在钱氏自己心目中,他可能更多属于中国传统之“文人”。这恐怕就非于连所能“理解”了。
但将钱锺书捧上“神坛”,称其为“最佳典范”(《中西文化研究十论》,第123页),也表明中国学者多少缺乏些“省思意识”。一则钱氏的著述虽然使其“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但其体例方式都属于“不世逸才”,不能成为“常规范式”。后人往往徒有“向往之心”,难具“效仿之行”;二是钱氏的可贵在于他对西方学术范式的自觉省思,而非仅在博征西方材料的满纸金玉;三则从整体建构来说,于连说其“无建构”也并非毫无道理。这一点,在钱锺书虽然是其理论思考后的自觉选择,但见地仍不能算高明,不如师辈的陈寅恪。陈寅恪早年留学多国,娴熟于西人学术,但其最可贵的学术特点仍在“以小见大”“以人带史”。但具体入手处是一回事,思维见地又是另一回事。譬如他就曾有过撰作《中国通史》《新蒙古史》的想法,没有做到是憾事,但思路本身,就表明他建构体系的意识还是有的。至于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他(指陈寅恪,笔者注)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俞大维语)
学术争论是好事,但彼此应当都尽可能树立起明确的“建设性意识”,在“学术性论争”中将思想推向深入,而非仅仅停留在空泛的中西立场之争上。从这一点上说,于连的思路进径其实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颇有启迪意义的小窗,或者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平台。对于现代学者来说,自觉理解和思考各主要文明的盛衰历程,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也确实需要各国学者来“共思”并“对话”。返而观之,在现代中国,我们缺乏对外国学有深湛研究而后又立足于“中国本位”的深层思考。于连的路径或许可以给我们些许启发。
另一位著名的法国汉学家巴斯蒂,曾谈及自己和于连虽同治汉学而方法不同:“确实不同,于连非常聪明,文章也写得非常好。原来他的教师资格是古典文学,后来他利用中国古代文学与希腊古代思想比较,推出了不少新思路。他是用思想、理念做文章,和我们用材料做文章不一样。他的研究自有他的价值。如果有人可以创造一些新思路,这是很好的事。”(顾钧《巴斯蒂教授访谈录》,载《国际汉学》第12辑第51页,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话说得很客气,但只能当作语者的礼节与大度看,言下之意则需要细加推敲。前者是以史料为根据的“学术研究”,从“材料逼出思想”;而于连则主要驰骋于哲学家的思辨领域,以“思想带出材料”。这是最根本的差异所在。不过,世上又哪里有绝对的真理呢?譬如,于连就给中国人塑造了一套理念:“工作、家庭、祖国。”(第362页)认为中国现在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再加上“古板的民族主义”。甚至会认为,十七~十九世纪,欧洲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已扮演完了历史角色,而现在则“注定会被超过。”(第361页)也就是说,他认为二十一世纪后的世界,很可能是中国或东方的世界。但细加考察,于连这种说法更多是“自我演绎”,既不能算是学术话语,更谈不上对中国文化的深层认知。
于连最后追问了一个问题:“不采取立场,我们能不能思考呢?”(《圣人无意》,第213页)这又是一个哲人的命题。值得指出的是,法国思想与政治精英有一种相当良性的互动,虽然矛盾也不少。现任总统希拉克就极为关注本国文化地位,正是在他的身上,人们似乎约略可以想见法国日后的振兴。更何况,还有如此让我们着迷,值得深加挖潜、至今仍领世界风骚于一时的“法国思想家”们。
此书的翻译瑕疵难免,如将德国人斯宾格勒称为“法国思想家”。(第362页)我想这应是一个简单的笔误。至于吉尔克加德(第112页),未注出西文,就不知所云了,但既与“卡夫卡”同列,我揣测也应是同类的思想家或作家,后查到原文,当为克尔凯郭尔(Sj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
(《(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法〕弗朗索瓦・于连、狄艾里・马尔塞斯著,张放译,大象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8.50元;《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法〕弗朗索瓦・于连著,闫素伟译,商务引书馆2004年9月版,13.00元)
